|
2011年初,我在上海创立巨鹿移动。当时我以为,聘请到优秀的工程师是件很容易的事儿。因为,中国每年会新增60万工程类毕业生,而且,我曾在谷歌担任产品经理,我很清楚如何吸引毕业生。
不过,我很快就意识到,在中国要雇佣到最好、最聪明的工程师,远比我想象得难多了。以我在美国硅谷的经验,最优秀的工程师通常都会选择最为大胆的挑战,因为,更大的挑战意味着能更好地证明自我价值,并相应获得更大的回报。尽早加入到创业公司,就是这种令人兴奋的机会、也是可能通向荣光的道路。
但在中国,我发现,占主导地位的却是另一种不同的心态。当我开始为新公司招聘人手的时候,应聘者总是撇开公司战略问题,先问我“公司能给多少薪水”。他们想知道,我的计划是不是实现上市(IPO)。
曾有一位应聘者告诉我,他希望得到“七位数”的薪酬(以美元计算)。他们虽然对我们公司在中国移动市场上的计划很感兴趣,但这些年轻人首先关心的,还是自己能赚多少钱、能获得怎样的名声。
他们未来会成为富翁,我们公司未来也会发展成著名企业,但我该怎样向他们证明这些呢?我并不怪罪他们怀疑这艰辛的创业,但让我震惊的是,比起我在硅谷合作过的工程师,这些未来的工程师竟然全然不愿冒险。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才开始明白为什么。
如今的中国年轻就业者都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出生成长起来的,他们生来就经历着中国经济年均8%-12%的快速增长,目睹着周围财富的惊人增长,也憧憬着这种事儿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他们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下的一代,有时也被称为“六袋弟子”(the six pocket generation),因为他们从小就生活在两个父母、四个祖父母的关爱之下,从小就被指望着能有好成绩、好工作。借助长辈们近乎无条件提供的资源,中国的年轻人从学校毕业、进入国际顶尖公司之后,都希望能够快速获得提拔,实现收入快速增长。
然而,中国经济前所未有的机遇,也让长辈们、甚至未来配偶们对年轻就业者产生了很高的期望。在中国“以家庭为中心”的文化中,老一辈退休后都依赖于后辈提供生活保障,这就给年轻人带来了巨大的薪资期望。
再有就是找对象、组建新家庭的挑战。我们公司某个关键岗位的一位应聘者,他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全球顶尖技术公司的工作背景,就在他都被聘用、正准备开始工作前的一个星期五,我接到他一个紧张兮兮的试探性电话。他吞吞吐吐地解释说,无法如约来上班了,因为他女朋友的母亲(未来丈母狼)认为,他加入我们这种初创公司太冒险了,他得找一份“稳当”的工作。我当时就震惊了。震惊就震惊在,他居然是以未来丈母娘的解释来作出决策的,居然认为这种理由充分合理足以推翻之前的决定。
不过,对中国的年轻男性来说,有稳定的收入和财富积累(如房产),往往是婚姻、甚至是约会的先决条件。中国人口结构已发生了显著的性别失衡,男女比例为119:100。这意味着女性能拥有越来越多的选择权,他们会倾向于选择那些有稳定收入、事业有成、拥有家产的男性。
这种强调稳定的文化,与商业环境所需要的文化心态格格不入。中国的年轻女性不用像男性那样面对住房压力,他们只需面对寻找富裕配偶的压力。(除此之外,不幸的还有,就像全球其他许多地方一样,中国也很缺乏女性工程人员,所以,我的招聘过程中,也很少有女性来应聘。)
另外,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导致了物价飞涨,尽管年轻人收入日益增长,但财富积累已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这个“以房产论成败”的国家,房价收入比已在全球最高之列。例如,在北京,自2005年以来,普通公寓的房价已增长了3倍,是家庭年均收入的27倍,是世界平均收入水平的5倍。因此,那些从长辈们那里获得巨大资助、买下房产的年轻人,自然而然就增加了薪资压力。
但对于像我这样的企业家来说,很难像本地公司那样,给“准员工”提供额外的福利。即使是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等成功的互联网公司,对此也有严格控制,其IPO的收益大都流向了高层管理人员。对于我们这种规模较小的公司,鲜有收购记录可以让员工乐观地认为,自己能有退出获利的机会。
为了克服这些因素,我学会要更多地关注个人和家庭的雇佣动机因素。我会花大量时间来解释,如果公司成功了,员工会得到什么样的经济利益。我们也提供优厚的住房基金,帮助员工支付首付。我们还会邀请员工的女朋友或家庭其他重要人员来参与公司的所有活动。我也明白了该如何招聘那些更看重技术挑战、而不是赚钱的应聘者。
中国是一个充满潜力的市场,会有更多的成功创业的商业故事,我想未来会更容易招聘到最优秀的人才。
| 注解说明:本文著作权属于原作者所有,只限于学习分享,不得用于任何商业用途!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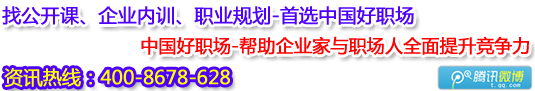
 儿童小学生幼儿园凹槽练字帖适合3-8岁儿童练字启蒙教育
儿童小学生幼儿园凹槽练字帖适合3-8岁儿童练字启蒙教育






